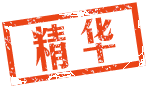|
|

楼主 |
发表于 2012-10-26 22:42:43
|
显示全部楼层
九九二大 老大和大师兄
老大 张宏宇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99级本科生 2000年7、8月间一个人骑车从厦门到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行程5000KM。为“拯救藏羚羊,保护长江源”宣传募捐,前后共为野牦牛队筹集资金5000余元。02年、03年分别攀登启孜、唐拉昂曲,任登山队队长。
(以下摘自老大在协会论坛上的登协英雄谱)
鲁迅说画一个人莫过于画他的眼睛,可老大的眼睛实在没什么明显特征。若真是有特征,还是他那两道极黑极浓的眉。老大的身材也很单薄,一点都没有草莽英雄的架势和北方人应有的彪悍。然而这单薄的躯体里藏着一颗怎样的心呢? 永不枯竭的动力制造机。身为会长,身为老大,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大家的热情,保持登协士气的高昂,让登协的骨干们永远充满干劲。在老大眼里,一切不可能都有可能,换句话说也就是毫无理由地乐观。登协也曾遇到过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也曾面临散伙的危险。比如2003冬训后开学,先是阿姨要辞职,接着是学校有令要登山先退学,再是“非典”给登山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大家会泄气,老大也会抱怨,但他很快先把自己的气打足,再去给其他人鼓劲,给他们动力,永不枯竭的动力。学校不让登山时陈晔曾问“你还能继续创造神奇么?”,最后他带领大家去了,大师兄谓之“顶风作案”。(此举是否合适留待后人评论) 永不泯灭的童心。老大信奉汪曾祺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保持一颗童心”。老大一直自以为“是很可爱的”,曾这样质问伊娜:“你难道不觉得我很可爱么?”看看当时他那一脸大胡子,谁听了这话不会晕倒?然而,在苏醒眼里,老大是“巨可爱的”,因为他们一起经历过最最单纯的佛耳山之行,那是一次类似小孩子过家家的玩耍,也可以说是登协的处女行。登山队中的老大呢?——我们在西大滩的小客栈一等,似乎修车就是遥遥无期了。我给阿姨发了短信。老大凑过来:“阿姨回你什么?”我看见老大“妒嫉”,偏偏不给他看。老大恨恨地瞪着我,这时候他的手机响起来,他一看,欢呼起来:“阿姨给我发短信咯!”那时的他真像一个撒惯了娇的孩子。——摘自夏茜《2003唐拉昂曲队记》 登协是条贼船,一上来就下不去。身为船老大,老大“骗人”的功夫可想而知。没加入的能让他加入;加入的干得久了、累了、倦了,想退出了,老大能让他打消这念头并重新焕发出激情;即使真的退出了,路上偶尔碰上老大,也会产生回来的冲动。所以柱子曾说“老大是最会骗人的”,没办法,做思想工作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登协的发展壮大啊。登协人都很能聊天,老大为最,而且最擅长聊通宵。芙蓉湖边、嘉庚广场、嘉三地下室、白城沙滩、还有柱子家里,一瓶1.5L的矿泉水,一条大“特香包”,就能聊一个通宵。(老大老是吃不饱,其名言“打出生的那一天起,就没吃饱过”,故经常抱着一条大“特香包”啃,众人为其冠名“面包王子”。) “能省就省,能借就借,能蹭就蹭”,语出老大,他也是最身体力行的。登协很穷,老大更穷。于是他带着大家一起蹭,去福州时蹭福州大学的学生宿舍,第二天人家学生会礼貌地把我们请了出去,就接着去蹭阿卓俱乐部的地板,顺带还能蹭岩攀。可气的是他还蹭自己人,柱子自是首当其冲,而哪个在芙二吃饭的人没被他蹭过饭卡?那是最穷的日子,毕业前一个月,把马拉松挣来的三百块花光,他已身无分文,连手纸都要用废复印纸替代。那段时间他的口头禅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毕业时学费没交拿不到毕业证,又厚着脸皮向婧姝借了四千块去赎证。2002年登山前,他从家里“骗”来的八千块学费都垫作启孜的登山费用啦。 登协的男生唱歌少有不跑调的,老大则是发自肺腑地跑,而且还是个“句歌王”。
大师兄 杨锋伟 厦门大学美术系99级本科生 2001年10月间从川藏线进藏采风,写生。02年、03年、06年分别攀登了启孜、唐拉昂曲、念青中央峰。
(以下摘自老大在协会论坛上的登协英雄谱)大师兄也是很会骗人的,直至今天都有人以为他真的是南普陀佛学院的硕士。因为他在登协不外乎两种形象:一种是光头;另外一种是光头刚刚长出头发。就算他是佛学院的,恐怕也终生毕不了业——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花和尚,抽烟、喝酒、嗜肥肉,还画人体油画,尤其擅长“美女走光图”。 然而大师兄又是极有人格魅力的。他做人是那样亲和,又是如此本分和不事张扬。骑自行车到福州时原计划是要攀登鼓山的,可到了之后才发现鼓山下面是个已完全商业开发的风景区,顶峰却驻有军队,是不可能让我们登顶的,遂取消了攀登计划。大家也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还拿出会旗和队旗在福建电视台摄象机的跟随下往山腰的涌泉寺爬去。大师兄这时候站出来说话了,要求把“厦门大学登山队”的旗子收起来,还要求记者在报道时不能出现“登鼓山”这样的字眼。是他,大师兄,在必要时刻保持了我们严肃意义上的“厦门大学登山队”的称谓和内涵,避免了我们沦为“爬山队”。 启孜登顶成功,回来后在学校搞照片展览。大师兄很认真地对我说,凭咱们的摄影水平,这不能叫“摄影展”吧。遂定名为“厦门大学登山队成功登顶启孜峰图片展”。而其实,我们三个负责摄影的用的都是单镜头反光照相机,也都是有一定的摄影功底的,相比于那些拿着傻瓜相机拍个活动就要搞个“摄影展”的,我们不知要专业多少。可我更知道,我们的确谈不上专业的摄影。 《厦门日报》报道我们成功登顶启孜峰,主标题“厦大学子初恋雪山”,旁边还有三个引题:“他们是国内仅有的六支大学登山队之一”、“他们与北大登山队同时从拉萨开拔”、“他们成功登顶又平安返回”。发稿之前记者有给我发E-mail让我审了一遍稿,我只校正了几个硬伤便同意其发表了。几天后,大师兄在我面前提起,日报用的那三个引题,虽是事实,却容易引起人误解,以为我们比北大登山队实力还强呢(北大那年山难),你怎么不让记者把它去掉。我哑口无言。当时我也有这方面的担心,可我没有去认真对待。 这就是大师兄,务实、严谨、不事张扬。是他的不断提醒,避免了我们协会沦为一个浮躁的、追求功名的社团;避免我们的攀登沦为一种亵渎神圣的“征服”;避免我们把登山当作一种炫耀;使我们还对得起“登山人”这个称号。为此,我敬重他。 大师兄还喜欢游泳,喜欢在沙滩上把皮肤暴晒成酱黑色,虽不及非洲土人,却也能使牙齿变得美白。其实,在登协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和大师兄在白城沙滩就有一次邂逅.那时我还不叫老大,他也不叫大师兄;那时我还没有留长发和胡子,他也还没有剃光头.我的小腿之粗在登协该是闻名的,没想到在沙滩上也有人欣赏,这个人便是美术系的人体模特,自告奋勇教我游泳的一位老爷子.他当然认识大师兄,便也介绍我们认识,可惜那时我俩只是象征性地彼此点了个头.一直到后来有了登协,举行过好几次活动,偶然的机会,我猛然想起这段往事,果然得到了大师兄的证实.便一起感慨上天的造化,登山给我们的缘分. 当然,大师兄更为人所熟知的还是他的幽默滑稽。柱子笔下的“冰镐打针”、“坐坏冰爪”故事已深刻刻画了这一点,我不多述。
|
|